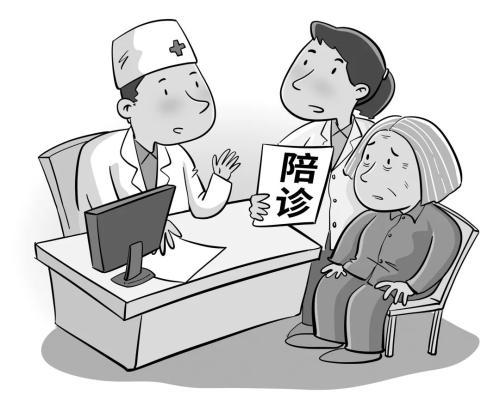
穿梭于医院、帮忙挂号取药、协助与医生沟通、陪伴就诊并提供照顾……近年来,“陪诊师”成为新兴职业,陪诊行业及其背后的“陪伴经济”也逐渐走进公众视野。陪诊师们在扮演患者临时“家属”、全程提供陪护服务的同时,大量陪诊服务机构也应运而生。根据公开报道统计,2022年,中国提供陪诊服务的企业数量已到达260家。陪诊师能帮助我们做什么?陪诊服务能撬动多大市场?
医院里的临时“家人”
“我今天接了两单,都是外地老人来北京看病。”《环球时报》记者联系上陪诊师邹青时,她刚刚结束一笔订单:一位河北的老人需要来北京做心脑血管检查,她陪着取号、排队、缴费、取药、辅助问诊等,并帮忙规划了下次就医的流程。邹青告诉记者,她下午还有一单,是一位来自河南的老人。
邹青是一名90后,从事医疗相关行业。去年,她了解到陪诊师这一职业,发现收入还不错,于是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做起了兼职。“因为我对医疗领域比较了解,所以这个工作上手还挺快的。到目前为止,基本我每周都能接到订单,收入情况也不错。”她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陪诊的主要服务对象中,有一大部分是来自外地的患者。数据显示,我国医疗资源存在区域间不均衡的情况。异地患者对大城市医院的就医流程、挂号方式、医院科室楼层、专家出诊时间、医院擅长领域等都不熟悉,从而希望寻求陪诊人员的帮助。而陪诊师的出现,可以在提供帮助的同时,让异地就医的患者在时间管理层面更为可控。
“从年龄角度来看,寻求陪诊的人员中,以老年人居多。”邹青告诉记者,需要陪诊服务的“客户”中,有很多是缺少子女陪伴的老年人,而负责“买单”的往往是子女家人。随着医疗服务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一些高龄老人来说,连最基本的挂号、取药事项都非常困难。如果儿女不在身边,就只能找人来陪诊。
正因如此,陪诊师常常会在工作中成为服务对象的“临时家人”,安抚他们的情绪。尤其是在患者遇到复杂病情,或需要面对一些诸如CT、核磁、肠胃镜等易引发紧张情绪的检查时,陪诊师们还需要给予服务对象关心和鼓励,帮助他们缓解紧张的心情。
付费服务也有伦理挑战
赵静也是陪诊师大军中的一员。与邹青不同的是,赵静服务于某专业陪诊平台,陪诊师是她的全职工作。“我们并不帮忙挂号,只是陪诊。”赵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陪诊师有很多工作都在“陪伴”之外,比如提前了解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熟悉本地各大三甲医院的基本情况和重点科室、擅长领域,并摸清各医院的内部布局和就诊流程,合理规划就医行程,以便顺利就诊。
“有时患者需要做核磁共振等需要预约的检查,我们还要提前去医院,帮忙踩点、预约检查时间。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把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不让他们白跑一趟。”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盘和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陪诊师并非“门槛低”。相反,专业陪诊人员须储备必要的法律知识,熟悉就医流程。陪诊机构也应对雇员做好审核、加强组织和管理,不断推动相关行业的专业准入标准和持证上岗制度。
在社交媒体上,陪诊师往往伴随着“高薪”“自由”等标签,但赵静表示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天大概能接两单,上下午各一单。由于每个服务对象要做的检查不一样,所以服务的时间也并不相同,但就我的经历来看,为每个患者的服务时间约为4小时左右。在收入上,公司定价是每单300元,我们抽取70%的提成,每单收入约为210元。”
2022年,国内媒体发布的《陪诊师职业调查报告(2022)》显示,近七成受访陪诊师平均每周陪诊不超过10次。且每一单的平均工作时长也不短,导致每天的接单量受到限制。近九成受访陪诊师月均收入在万元以下。
尽管是付费服务,但在陪诊过程中,陪诊师们会不可避免遇到来自法律法规及道德伦理方面的挑战,比如陪诊师能否代替家属进行签字、如遇紧急危险情况该如何决策等。赵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陪诊服务开始前,双方就会签订合同,明确各自权利和义务,避免产生这类纠纷。对此,盘和林也认为,陪诊师在服务过程中会遇到很多个性化需求,需要与患者家属签署协议,在协议授权范围内履行职责。
行业前景如何
陪诊行业的市场增长潜力来自不断增加的就医需求。一位医疗从业者在采访中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如果陪诊师具备足够的专业性,可以成为患者和医疗系统之间的桥梁,甚至能缓和医患间因沟通不畅引起的矛盾纠纷。
与养老需求的结合也是撬动行业潜力的重要发力点。“年轻人没有时间陪老人看病,所以就有了陪诊师。陪诊师属于特别需求,目前市场空间不大,但随着老龄化推进,预计需求会有所增长。”盘和林表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陪诊行业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在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陪诊服务产生需求。这一产业也可能会走向纵深,服务内容也将进一步多样化。比如,现在只是陪着去医院,未来可能会向全流程服务的方向发展。”
作为新兴职业,“陪诊师”目前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2022年10月2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陪诊师”这一职业仍未被收录在内。在准入门槛、服务流程、服务质量、争议解决等方面,陪诊行业也尚无相关法规及政策规范,收费标准也未有统一要求。
《环球时报》记者致电几家陪诊机构了解到,一些正规的陪诊机构会要求陪诊师考取社区健康管理员的证书,持证上岗。有的甚至会要求陪诊师学习医疗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在帮助职业陪诊师规范发展的同时,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记者也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机构在工作流程、收费标准上都无规可依,服务水平也良莠不齐。与此同时,行业内不乏个人接单的陪诊师,他们大多是时间充裕的自由职业者或大学生,缺乏相关行业培训,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相关信息,招揽生意。此外,一些“黄牛”也打着“陪诊”的旗号混入市场,获取不当收益。
盘和林补充道,中国社会未来老龄化趋势无可回避。在这种趋势下,子女忙于工作,陪诊或将作为陪护的延伸业务,成为老龄就医人员的刚需。对此,需要从业人员的素养不断提升,更需要行业整体的统筹规范。
“为了使行业健康发展,未来陪诊师需要在服务方式、服务内容、责任界定、定价等方面强化规范管理。虽然我们没有专门的关于陪诊师的职业规范,但也可以通过借鉴的方法来规范行业的发展。”李长安称,对于需求方,尤其是老年人来说,需要从正规渠道获得服务,使自己的需求获得高质量满足的同时,不陷入纠纷,甚至被欺诈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