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考古机构排名前十(成都的考古遗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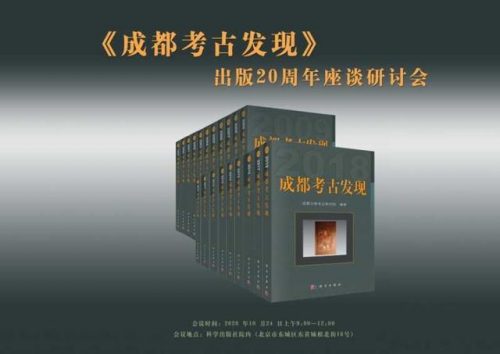
靳小沛 四川在线记者 吴晓铃
提到成都考古,人们往往会第一时间想到被作为成都城市标志的太阳神鸟,以及成都博物馆的网红石犀。这些文物,都是近20年里,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考古工作中发掘出土的。

自成都金沙遗址在2001年被发现以后,成都考古新发现的20年“黄金时代”中,究竟取得了哪些令人瞩目的成果?10月24日,《成都考古发现》出版20周年之际,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科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组织召开专家座谈研讨会。专家们一致认为,成都众多重要考古发现的接踵而至,改写着人们对成都历史的固有印象。成都考古成果一次次拓展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广度与深度,传承了巴蜀文明,不断拓展着天府文化丰富内涵。

黄金20年 成都考古硕果累累
“成都考古近20年,在全院考古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直言。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的发掘成为古蜀文明研究继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成果。代表“王者”身份的金面具、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的太阳神鸟金箔、来自于良渚文明的十节玉琮、色彩斑斓的各类玉器……构建了一个神奇、充满想象力、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被誉为本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
金沙的发现开启了成都考古的黄金年代。
从2001年开始出版的考古院年度考古报告集《成都考古发现》(1999~2018)不难发现,这套丛书已发表考古调查、发掘与分析报告425篇,总字数近2000万字,开创了国内考古报告集年度出版的先河。。时代涉及先秦至明清各个时期,内容包括遗址、墓葬、窑址、摩崖石刻等,并有相当数量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报告涉及区域涵盖成都平原、川西北高原山地、川西南山地、川东北地区、三峡地区等地域。

先秦考古中,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大邑高山等史前城址及金沙、十二桥、新一村、商业街船棺都是公众熟悉的考古项目。商业街船棺墓,一度因为出土大量船棺以及修复完成“古蜀第一床”而受到公众关注。
秦汉以后的考古更为公众熟悉,在成都市中心发现唐朝中央公园摩诃池,明朝蜀王府遗址被发现以及春熙路江南馆街遗址等等,重塑着古代成都。今年在新川科技园发现的数千座墓葬,更是成为公众一时关注的热点……
在考古之外,成都考古还在科技考古方面不断突破,4000多年前成都人就吃上水稻等植物考古成果,让普通百姓对考古也能产生浓厚兴趣。
正是一个个扎实的考古和科研成果,共同汇成了《成都考古发现》。

专家点赞成都考古
在考古资料科学管理工作中,年度报告的编辑出版是一种及时、系统科学准确的形式。在《成都考古发现》出版20周年,专家们如何看待这项学术成果?
在24日的专家座谈研讨会。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副司长张磊,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王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书记陈建立,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等就此展开研讨。

专家们一致认为,通过20载年度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对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科研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结起来至有三方面:一是田野考古资料公布的时效性。一般的考古发掘材料均可在发掘后的第三年见于年度考古报告集。二是资料公布全面、详实。不受篇幅和材料限制,鼓励全面、详实发表考古资料,一方面促进了新资料及时消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积压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得以最大释放。三是对于提升年轻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发掘水平和研究水平有着积极作用。在《成都考古发现》的审稿与编辑过程,往往发现许多问题,有些是田野发掘中存在的问题,在些属于报告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后及时与本人直接沟通,许多年轻人的田野发掘和报告撰写水平因此得以明显提高。
据介绍,鉴于《成都考古发现》主要收录本单位历年完成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多为基础性考古资料,缺乏更深层次的研究。因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还编著了系列学术集刊《成都考古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2009年创刊,目前已出版4辑,收录考古院研究人员历年发表的各类研究性文章共计160篇。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出版有《宝墩遗址》、《成都十二桥》、《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金沙阳光》、《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成都包家梁子墓地发掘报告》等考古专刊报告逾50部,成都考古研究丛书专著3部,资料集成20余部,图录20余部。此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还与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四川大学博物馆联合复刊了童恩正先生创办的《南方民族考古》学术集刊,也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现在已出版至第18辑。

